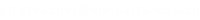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
校刊编辑室 主任
kghjkhjlk - 彭 碧仙
头顶的蓝天
——各拉丹冬探险纪实之一
题记:“我认为,要通过人,通过有生命的东西来寻求真理,这是我主要的见解。”
第一章准备阶段(三月聚粮)
第一节我---车上的灵魂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使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法]玛格丽特·杜拉《情人》
正如我花费很长时间才理解我对度过童年的贫穷世界的依恋与热爱。
天空是蓝色的,通风的。
[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这是以实玛利随船追猎白鲸,亚哈船长和其他伙伴船毁人亡,他自己侥幸脱险以后的话。在1994年春天,在我开始准备攀登长江源头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冬(6621米)的时候,我很少去想其中的风险,很少去想和这个水手一样的死里逃生。
在这以前,我的野外经历是丰富多彩和充满趣味的,虽然艰苦,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生命危险。
我有过一、两次山间生活的经验,不过都是得自3000-4000米之间的土石山峰,不是冰雪山峰。其中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是1988年秋天和三位同学王智利、朱挺松、范新海一起攀爬秦岭主峰太白山(3777米)。由于有隔壁宿舍的同学失败在前,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器材和食品:一架望远镜、一个5000米高程的瑞典制测高仪、两台手动相机、两把刀、四个地质包、十斤烧饼、四个罐头,还有羽绒服。我们从公路下车,首先徒步20公里到达太白山南坡脚下的小村庄厚畛(畛:小块土地的意思),饱餐、休息一夜。第二天上山,在淋漓雨水中到达半山腰,夜宿破庙。第三天一鼓作气,突击冰雪覆盖的顶峰,从一面是山岩,另一面是山涧的小路翻越太白山,到达北坡的半山腰,休息一夜。第四天,路经“斗母宫”,安全下山,返回西北大学。
在这次攀登中,我们一共徒步行进四天,行程100公里。我第一次体会了连续行进,攀登和跋涉的感觉。在山中,两件事情让我懂得了判断力的重要。
一次,是行进中的第二天,因为在休息的破庙周围没有找到大一些的水源,我开始四下搜索。遥遥地听见破庙前面的山谷里水声隆隆,我拿起自己的刀和大家的水壶下山谷找水。无论怎么走,那水声好象总在我前面远远的地方,起初我没有在意;后来,越走道路越窄,我必须用刀开路才能穿过密密的灌木丛,我不禁疑惑,如果这是打水的路,怎么这样难走?这时候,一阵冷风吹过,水声随之骤然变大,就象在我面前一样。我忽然意识到,我一路而来听见的不是水声,而是松涛,是山风吹动秋天的树木,树木摇动的“沙沙”声汇成的轰响。不知道为什么,一阵巨大的恐惧象闪电一样袭上心头。就象有人和野兽在后面追我一样,我挥刀劈开眼前的路,没命地向上向破庙爬。直到看见我的同伴,我的心跳才平缓下来。直到后来攀登各拉丹冬左侧山脊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形的石头,甚至直到今天回到城市平静温暖的生活中间,我仍然难以忘记在山野间,在孤身一人的时候,判断错误的时刻能够给人带来的那种恐惧。
还有一次,在第三天,突击顶峰的路途中,在一处开阔地,我们遇到明显的岔路,三条道路摆在面前,我们四个人的意见又是南辕北辙,各不相同。我忽然想到挂在我胸前的测高仪。我拿出它对大家说,如果我们按照眼前道路走下去越走越高,就有可能是对的,如果我们越走越低,那就是错的。四个人拿起地上的背包按照我选择的道路向前行进,测高仪上的读数不断上升着,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看见了太白山顶峰下面水凉刺骨的深潭“大爷海”,然后是顶峰。这次的经验告诉我,精良的仪器至关重要,在我们出于地形、阻隔、视差和天气原因无法正确判断的时候,无言无语无喜无怒的工具常常是忠诚的伙伴。我再一次感觉到工具、器材的重要性,是六年以后攀登各拉丹冬,使用那支意大利冰镐的时候了。
比起跋涉和攀登,我更熟悉的是八十到九十年代流行的自行车越野。
我第一次骑车出门是1988年,当时,我从西安出发,一人一车,穿过黄土高原的陕西、甘肃和宁夏,直到新疆的善鄯,除去中间搭车越过一段戈壁以外,总共骑行2400公里。在新疆的烈日骄阳下,车轮的外胎开裂,我被晒脱了数不清几层皮,回到西安以后很久,换过几次皮以后,皮肤才恢复原来的颜色。
这次骑行在技术上平淡无奇,但是,它让我第一次离开城墙围绕、人声鼎沸的西安,看到了、感觉到了真正的西北:辽阔、贫瘠、烈日和干渴下的西北。
多少年过去了,我都坚信这样一个模糊的想法:每一个只身漂泊、闯荡野外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家”可能是你生长的地方,也可能是你梦想中的地方,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你会觉得生而快乐,也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我在漫长的旅途中一直讲一口陕西话,也许是陕西人遍布西北,也许是陕西口音和甘肃、宁夏、新疆的口音接近,总之,这种刚硬的方言把我和甘肃、宁夏、新疆的一个个每晚住宿费两块钱的小旅店、一个个卖炒饼和面片儿的汉族、回族的小饭馆联系起来,把我和生息在那里的脸膛红红的男人和女人们联系起来,把我和六盘山的弯路和看过去几天几夜都是一样的沙漠戈壁滩联系起来,把我和宁夏山坡上的小伙子一边挥动大锤打石头一边光着上身唱出来的“花儿”联系起来。
我接近甘肃泾川的时候,在盘旋着的山路上,碰到一个卖鸡蛋和茶水的老太太,一眼望去就知道,她的家在这座山下深深的沟里,她是挽着篮子,篮子里装着水壶和鸡蛋一步一步从深沟里爬到公路上的。鸡蛋是煮熟的,茶水则是用树叶泡出来的,只有颜色和苦味。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方,水贵如油。可是我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告诉我,喝一大杯水,只要两分钱。她不知道,在这样烈日当空、焦渴如火、空无一人的山岭上,其实她卖得再贵二十倍,过路的人们也不会拒绝。我看着她盘腿坐在路边,看着她脸上的笑容、皱纹和一双缠过的小脚,看着她从提上来的水壶中倒出满满的一杯水,我的泪水涌上眼眶。
西北。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和离弃的“家”。
每次想到为什么我能够从1994年那样深重的伤痛和危险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也许,在一次次的远行中,我一次次地积累着爱和留恋。既有对我的父母和朋友的爱和留恋,也有对西北这片贫瘠、荒凉、广阔的土地的爱和留恋。这些爱和留恋将会牵引着我走出绝境。
198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宿舍的范新海骑车去东北和内蒙古,准备去“看草原”。当我们骑行2200公里,到达大庆的时候,范新海去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地点---石油管理局报到。主管报到的人发现范新海没有西安到大庆之间的火车票需要报销的时候,一度非常疑惑。当范新海告诉他我们是骑车“来报到”的时候,这位和善而懒洋洋的工作人员瞪圆了双眼,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听错。
由于范新海的急病,他被迫放弃了继续前行、进入内蒙古的计划。从大庆开始,我独自一人骑向草原,从扎兰屯进入内蒙古,先后骑过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深入科尔沁草原,探访那时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霍林河。最后,在人车俱损的情况下(车头已经颠簸得变形),我在通辽以西120公里一个叫做“八仙筒”的小火车站,放弃了原定6000公里回到西安的骑行计划。
那次,除了饱览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风土人情以外,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深藏在自己身体中的潜力,体验到自己的体力发挥到极限的时候可以达到的惊人效果。在短短的25天之内,我一共骑行3400公里,除了在草原上以外,每天骑行150—180公里,最快的一次,一天之内从辽宁省的沈阳骑到吉林省的四平,208公里。不过,这样高速强劲的越野骑行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在哈尔滨称体重的时候,我1米78的身高,只有108斤重。回到西安,我休息了一年才缓过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表现出过度疲劳的所有症状:饥饿(一顿饭可以吃掉一斤四两羊肉水饺)、干渴、注意力分散、嗜睡。
不过,我从这次越野骑行中看到的自己的潜力和爆发力,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它们鼓励我走得更远、更高。
对于我计划中的登山行动有直接帮助的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骑行,那次的目标是西藏。对每一个热爱骑车越野的人,对一个从很早就怀抱“一辆跑车,一壶水,一个背包,一顶太阳帽,走遍天下”想法的人来说,那片中国和世界上最高、最险峻、最独特的土地,是必然的最后一个目标。为了了解西藏,我阅读了西北大学图书馆中所有能够找到的书,包括传教士们的著作和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也去拜访了曾经在青藏线上勘探、开车的前辈。
1991年7月16日早晨,我用红色跑车的后轮重重地撞了一下西北大学的大理石校门,告诉前来送别的同学,一个月后,我要把这辆跑车的前轮浸入拉萨河的流水。那次骑行,让我熟悉了蜿蜒在雪峰下的青藏公路、熟悉了牦牛粪燃起的缕缕炊烟,熟悉了戍守在漫长寒冷青藏线上的解放军官兵。二十四天以后,当我把车轮深深地浸入拉萨河的时候,当我因为偶然的原因一个人坐在布达拉宫里面的木头楼梯上听着僧侣们吟唱似地诵经的时候,我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不知为什么,西藏总是让每一个历尽艰辛来到它面前的人都能感觉到:那里是自己的家。
那些靠在路边的里程碑上休息、吃罐头,面前是河水,远处是雪山的时刻;那些每走三步,双手合十,五体投地,全身跪拜,徒步几千公里直到拉萨大昭寺的信徒;那些收割了青稞以后,欢快地跳起锅庄舞,跺脚、旋转、歌唱的藏民,让我看到这片土地、这个民族沉默无言背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他们千年不灭。
有好多年,在图书馆的书桌前,在西北大学盛开的梨花树下,在梦中,我总觉得自己在骑行:在新疆酷热的公路上,在内蒙古退化严重、干旱发黄的科尔沁草原上,在昆仑山口、烽火山口、唐古拉山口的劲风和冰雹中……
我从骑行中认识了中国戈壁那样的广大、甘肃那样的贫穷、雪山那样的壮丽,我常常想,这是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地方。
不管离开骑行的日子有多么久,我还是觉得,我的灵魂在野外、在车上。
在散文《车上的草原》中,我描写过心中的这种感觉:
我骑行,每天上百公里地骑行,好象怀抱一种伤感,偶而叹息;又仿佛经历一种悲伤,为了上苍。推动自己骑行的,是一种音乐,就奏响在头顶这块阴沉的天空,又仿佛一种力量,无以名其形状。巨大的天空下,看不到边的平原上,仿佛从来就有了这样一幅画面,这样一种象征:长长的公路(黑色)、雪白的跑车、象西希福一样生来就在骑行的我。
轮下是水患初平的公路,身后是告别同伴时的天空(看不见白云),触摸着水壶和背包,才知道还有东西陪伴着我。一个声音象血缓缓从体内流出一样:我想去哪?另一个声音象金属,锐利地划破北方清晨的宁静:草原!我尖声地回答。
车子颠簸着,我扶住跳动的车头,依然骑行。从背包中取出饼干,细细地咬碎,慢慢咽下。一顿午饭,依然骑行。道路真静,恐惧时怀疑生命的实在,又有时,快乐地享受无所思想,头脑空空的宁静,这时的快乐让我流下热泪。
我于是知道自己将到草原,无论多么遥远,我也闻出了那种气息,刺鼻,难忍,然而,我爱它,爱这次骑行的终点,象爱一堆温暖的篝火。
天似穹庐。车轮下终于看见压死在路边的小蛇,飞扑到脸上的苍蝇顽强而挥斥不去。绿草一线,如天边的海。我抑制自己,按捺自己,象用双手、用全身遮盖在一面鼓上,为的是不让它过早地敲响、轰鸣,过早地泄露我饱满的欢乐。
牛群,羊群。草原如黄绿交织成的地毯铺满平缓的山山丘丘的眼前。穿着旧军装的青年,骑着毛色驳杂的马,驰到身前,我才看清一张四方的刚毅的脸,听到蒙古腔的汉语:“哪儿的?”
我喘一口气,摘下太阳帽。比乌兰浩特、比呼和浩特还要远,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来得那末快,又那末自然,犹如不知不觉走进越来越深的温水。就这样来到了草原。心中的鼓声并没有响起,看见蒙古包,骑过蒙古马之后,淡淡的,悠悠的,并没有奔腾的狂喜。
夜晚的旅店依傍着山,门前的主人医治着马伤。繁星满天,飘来羊肉煮炖出的香气,昏暗的电灯光似乎不比我旅途中的第一杯酒更浓。
主人睡了。我穿上所有的绒衣和毛衣来到夏夜的庭院,草原的寒凉中,是交织成一片而不分节奏、不知方向的虫鸣包围了庭院。是四周的虫鸣,而不是繁星,让我觉到了,我终于生活在一个四周充满生命的世界。
比起骑车越野,登山,需要另外的技能和同样的一种灵魂,那种包含着环顾四野的判断力和血气充盈的胆量的灵魂,车上的灵魂……

 (创新港)
(创新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