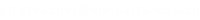导师Prof. Dr.-Ing. Dr. h. c. mult. Dr.-Ing. E.h. Günter Pritschow千古 - 首页
前段时间备课查资料,赫然发现我的导师Pritschow教授于2021年6月14日辞世了。2019年末为Y同学在国际生产工程科学院(CIRP)年刊发文的事给导师打电话时就已觉得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真在斯图加特大学机床控制研究所(ISW)网站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免难受。随即写邮件询问当年的同事,对方回应说老师并非死于新冠,而是因为慢性的心肺基础疾病,最后选择放弃长期住院治疗,在家平静地走向了永眠。我从小就不喜欢写文章,但是这个打击情憋在心里总是难受,想着倾诉些什么。
遥想2017年最后一次去Baden-Baden拜访导师,发现在他书架的角落里放着一本《我的奋斗》,便试探地问了一下。老爷子说,他是1939年1月出生在柏林的,出生后半年希特勒就上台了。他的幼儿时期基本都是在战乱中度过,在成长的历程中对那段历史以及两极分化的过渡产生了非常大的迷惑,所以在闲暇之余找了各方面史料进行了比对,也包括希特勒的自述。长大后的他进入了柏林工大Spur教授领导的机床与制造工艺研究所读博。毕业后导师在西门子的研发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84年来到了斯图加特大学执掌ISW21年,中途还去干了一届斯图加特大学的校长。科研之余,Pritschow教授精通钢琴和巴松两门乐器,颇有欧洲老贵族的风范,也曾经多次在学术会议的晚宴上助兴演奏。
导师读博那时正值美国去工业化,制造业开始向德国、日本等“廉价劳动力”战败国转移的时代,借此契机Pritschow教授与他的导师Spur教授、以及亚琛工大的机床实验室(WZL)主任Weck教授携手长期致力于数控机床在德国的推广与技术革新。可以说德国的高端数控机床能有如今的强势地位、甚至德国能成为现代制造业强国,这三位教授所领导的团队有着重要的贡献。也是因为这三位教授的联手,在广为人知的德国TU9联盟背后还有个在机械学科更为小众的ABS联盟,分指Aachen, Berlin和Stuttgart。在Pritschow的领导下,ISW科研领域从产线自动化到开放式数控构架、从数控核心算法到伺服系统的控制与驱动,几乎涉数控技术的方方面面。此外,他推动毕业生成立了专做数控核心算法与虚拟仿真的ISG公司,为Heidenhain等公司提供数控算法。正是由于这些卓著成就,Pritschow教授被授予联邦德国一等十字勋章,成为了CIRP,Leopoldina研究院以及Acatech的fellow。不过在德国时,老爷子从未主动提起过这些头衔,所里的同事们虽然会在私下揶揄称之为圣*教爷(教父的教),但也未必真正了解他的学术荣誉。我是在发文写作者简介时才查到这些,更是后知后觉的在2020年才在网上看到原来这个以人名Leopoldina命名的研究院在中国被译成德国国家科学院,而Acatech被译成德国工程院。
PS,我虽没见过师爷,但也听过他的归宿。2013年的CIRP年会在哥本哈根召开,Spur教授听完了一天的报告回宾馆休息,一睡就再也没有起来。曾经和一个同样有德国背景的学者聊天说起过这事儿。对方感慨到,死在学术活动中才是一个专家的幸福归宿,总比死在酒桌上的好。
我进入ISW是2010年的事,那时Pritschow教授已经退休,但遗留了一个面上(DFG)项目需要有人帮他扫尾。在经历了长期的职业科研生涯之后,晚年的Pritschow教授执着于提高伺服系统闭环带宽和伺服刚度,从根本上解决加工精度和加工速度矛盾这一难题。虽然那个项目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也就是因为接触了那个项目才确定了我今后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以此写了自己的DFG面上申请书。老师因为常住Baden-Baden来所里的时间不多,但每次来也不会有什么架子,会饶有兴趣的去各个办公室和人讨论。因为我做的是他的夙愿方向,来我这儿逗留的时间就会相较于其他同事多。曾经因为我德语不好产生了误会,老师用纸笔耐心地给我推导了一遍如何做Bode图以及高阶传递函数的近似方法。当我的面上申请被驳回的时候(驳回的理由竟然是与Pritschow之前的一个项目方法雷同)老师与我义愤填膺,连夜写申辩材料(是的,德国的面上有一次申辩的机会)。那时的我从未觉得自己德语能如此流畅,而老师更是把我的初稿拿过去改了一版更为强硬的措辞,让其他德国同时羡慕不已。曾经看我实验做到关键时刻,老头也一下也来了兴致,迫切想在回家前看到实验结果,亲自下场帮我装卸负载、拧螺丝,结果错过了回Baden-Baden的火车。也曾记得老师约我去他家修改博士论文,原本预计4个小时的时间,在导师逐段逐句地细致修改下拖到了7个小时,还在他家蹭了顿饭。
成果发表后,导师邀请我参加2016的CIRP年会。我第一次用英语作报告,又是如此重要的场合,难免怯场,正想着怎么让导师亲自上场,CIRP的前主席Altintas教授过来打招呼问导师什么时候的报告。老爷子指了指我说,今年他替我做,我年纪大了在下面坐着就好啦,你呢?Altintas回“哈,你是老家伙,我还年轻呢!”说完来了个爱因斯坦式的吐舌。我的报告讨论结束后,一位白发学者起身说道,看见Pritschow是你报告的共同作者,也跟高兴看到Pritschow教授今天在场,CIRP的Machine分会(STC M)能有今天,当年的主席Pritschow教授功不可没。STC M的时任主席Brecher教授(WZL的现任主任,Weck的继任者)也赶紧说道“是啊,您对STC M的贡献我们永不会忘。”紧接着会场内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老爷子起立点头向大家示意。我在台上又是自豪又是小尴尬,虽然不知道老师当年是怎样将STC M力挽狂澜的,不过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爷虽然归隐,但江湖上都是爷的传说吧。
PS,相较于只能写4页纸的年刊论文,CIRP的年会给足了每个汇报人30分钟的汇报讨论时间。与国内报告重背景与战略展望不同,CIRP的年会报告更注重科研的过程和对结果的分析(起码STC M是这样)。说的人是真的想教会听的人,而听的人里面也总有些人是真的会去思考说的人所做的细节。每场报过结束,台上与台下总能产生热烈的讨论。2016年我就遇到一位日本学者对我报告中传递函数的形态表示了不解,讨论了半天直到茶歇时给他推导了一边才满意的道谢离开。当时双方也没有互通姓名,直到2018年会时承办方主席上台发言,我才依稀意识到之前那位和我一起推公式的日本学者应该就是台上这位东京大学的光石衛教授。要不是财务报销要翻译邀请函,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人家叫啥。
博士答辩后的聚餐,老师悄悄和我说,我退休了,换了新笔记本后学校的MATLAB序列号不能用了,你能帮我装一个可用的MATLAB吗?这一任务也就成了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导师的原因。那次拜访后不久,我便回到了中国开始了新的工作。本想着2018年的CIRP年会还能在东京见上导师一面,但毕竟路途遥远,导师没有参会,再一次把报告的机会让给了我。安装盗版MATLAB那次,竟是永别。
科学家虽有国界,但是科学精神没有。从Spur教授到Pritschow教授,学生虽不敢说自己会有多大的科研成就,但会努力把这份对科研的纯粹传承下去。只要有传承的人,今后就必能点亮耀眼的光。


-
2022
07-07
-
2022
06-17

 (创新港)
(创新港)